專訪潘興斌教授:重拾對數學的敬畏

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回憶里一定少不了“數學”。從小學的算術,中學的函數與幾何,再到大學的微積分與線性代數,數學為學生們帶來了太多的歡喜與憂愁。可是我們對于真正的數學研究,仍有一定的距離感。大概除了“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等家喻戶曉的數學難題,大部分人對于數學理論的學習與研究并不了解。
本期為您分享第八期校刊《神仙湖畔》的人物欄目。我們邀請到了理工學院潘興斌教授,以及潘教授的幾位學生,帶我們重新認識數學領域的研究與學習。
人物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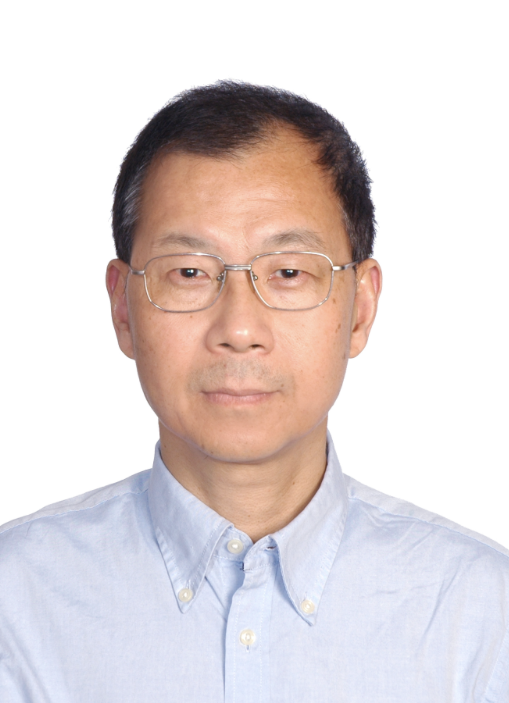
潘興斌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工學院教授
1987年獲山東大學數學系博士學位后在浙江大學任教,2004年受聘為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2006年1月受聘為華東師大終身教授,2007年12月31日起任二級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偏微分方程,包括非線性偏微分方程理論,變分問題,超導、液晶、電磁場的數學理論等。
潘教授主持的項目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8項、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項目、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等,已發表論文98篇。他關于表面超導數學理論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同行中有一定影響,1995年合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四等獎,1997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2000年入選浙江省高校優秀中青年學科帶頭人,2006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2年獲“寶鋼優秀教師獎”,2019年獲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一等獎提名),2022年度獲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模范教學獎。
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后,潘教授專門為大一本科生開設《微積分精講》系列課程,旨在為有志學習數學理論的同學提供進階數學理論的教學和更加扎實的分析學訓練。
?
1. 偏微分方程:
“描述真理的語言”
現代數學大致可以分為分析、代數、幾何三個領域。潘教授的研究領域為偏微分方程,是分析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世界萬物,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無不在時空中運動變化,考察這些運動與變化,往往可以用某些物理量關于空間與時間的變化來描述,這就是偏微分方程與方程組。因此偏微分方程是研究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重要工具。”潘教授如此形容偏微分方程。在2022年9月24日至25日舉行的“偏微分方程:分析、幾何與拓撲的相互作用”研討會上,潘教授引用了西漢劉安《淮南子. 齊俗訓》作為會議的結語:“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而這句話恰好詮釋了他對偏微分方程的理解。
在數學領域中,“線性”是一個相當良好的性質,因為它意味著對應問題易于研究、求解、定量分析。在常微分方程中,線性的理論已經得到了詳盡的研究,并成為了數學本科生必須掌握的基礎。相對而言,偏微分方程中的“線性問題”復雜許多,但仍有許多對應的求解方法。潘教授指出,“數學家發展了各種求解偏微分方程的方法,這些方法往往只適合于求解線性方程。而我們的世界是非線性的,大量物理現象是非線性的。當不能求解時,需要研究方程的性質,了解方程的解的性質。至今,對非線性方程的一般性理論和具體方程的定性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依然有大量重要問題沒有解決。”偏微分方程的定性研究方法往往與具體的方程組有關,而這意味著在偏微分方程領域,不同學者的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都會有很大差別。
說到偏微分方程領域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潘教授給出了堅定的回答:“與現實世界的深刻聯系。”訪談中,課堂上,潘教授總是強調,往往是“先有數學,再有物理”。潘教授舉出了兩個具體的例子。其一是俄羅斯的物理學家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阿布里科索夫。他在研究金茲堡-朗道方程時,通過方程的局部線性化,求解出對應線性問題的特征函數。而這些特征函數的零點正是后來經實驗證實的“阿布里科索夫渦旋點陣”。其二是物理學家皮埃爾·吉勒·德熱納。他在凝聚態物理學的研究中發現,一些不同的物理現象間存在數學相似性,所以研究簡單的物理現象的方法,可以推廣至比較復雜的物質形式。比如描述超導現象的數學理論,可以用來預測液晶的物理現象。而他也因此獲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數學結論與現實現象的深刻聯系。
作為一名數學家,潘教授非常重視數學理論在現實世界的對應。他主要的研究興趣是一些物理中重要的非線性偏微分方程,譬如支配超導現象的金茲堡-朗道方程、液晶的朗道-德熱納方程、電磁學中的一些方程等。“我目前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區域的幾何與拓撲對偏微分方程的影響。我也關注不同領域的物理現象在數學上的相似性。”數學理論中的不同分支與領域之間存在著廣泛的聯系,而這些聯系又對應著我們的現實世界。這些聯系與對應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世界真理的形態,也成為了潘教授研究的一大主要動力。
?
2. 數學研究:
保持敬畏,走出自己的路

潘教授在偏微分方程論壇上致辭。理工學院/攝
提及“數學之美”,我們腦海里總是浮現這樣的關鍵詞:對稱、簡潔、統一。不過,這些簡單的概括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不同數學領域的研究問題、對象、及研究范式,都會有顯著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也許會帶來領域之間不同的“美”。
提到“數學之美”,潘教授引用了楊振寧先生在一次采訪中提到的關鍵詞:“敬畏”。楊振寧先生曾在《人物》雜志的訪談中這樣說道:“對于自然的了解,當然是與日俱增的——可是這些與日俱增的里頭的內容,比起整個自然界,整個這個結構,那還是微不足道的。你也可以說年紀越大,這種對于自然界的敬畏感是越來越深。”對于數學領域,潘教授有同樣的敬畏,也正是如此的敬畏讓他擁有了對于數學的審美體驗。事實上,潘教授指出,敬畏之情是“一個學者的基本素養”。
對于數學研究,潘教授同樣有自己的心得。他指出,數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解決前人遺留下的難題,其二是發現領域內新的現象或規律,提出新的問題,并拓展該領域的邊界。對于后者,潘教授以我校的倪維明教授為例,提到倪教授“在‘區域的幾何對偏微分方程的影響’這一方面做了很多先驅性的工作”。在千禧年初,潘教授也在他的研究領域提出了自己的幾個猜想,其中一個猜想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里得到了同行學者的驗證。“在這個領域里,要么最早,要么最好。”這是潘教授界定一個優秀的數學學者的標準,也是他自己的學術追求。
最后,潘教授強調了一名學者在領域內進行學術發展的基本準則:“走出自己的路”。不論研究方式如何,對于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某一領域有自己的觀點或想法。
?
3. 數學教育:
因材施教,培養分析能力
潘教授在教育上頗有研究。他所開設的《微積分精講》系列課程得到了許多學生的好評,也為這些學生日后在數學領域的學習打下了重要基礎。
對于教育,潘教授引用了徐揚生校長的一句話:“本科生教育是一所大學的最重要的質量指標(沒有之一)。所以,我們要求每個學院最優秀的教授(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必須給本科生(尤其是一、二年級的同學)授課。”微積分,或者說數學分析,是數學本科生學習數學理論的重要基石。潘教授也因此對相關課程格外重視,并在長年累月的教學中形成了獨到見解。
《微積分精講》相較于普通的微積分課程,增加了更多的數學分析理論,并通過理論的學習與證明,訓練學生的分析能力。“本校有相當多學生有理想、有追求,有明確的奮斗目標。其中有不少學習能力強的學生,我們需要為他們提供更多優質課程,使他們更好地成長。另一方面,不斷培養優秀學生的數學基礎和素養,對發展我校的數學學科,也是至關重要的。”這便是我校開設精講課程系列的初衷。
事實上,潘教授的這門課程是數學系眾多老師在“精講課程系列設計”上邁出的第一步。“在倪維明老師和數學組其他教師的極力推動和不懈努力下,幾年來,我校在數學課程教學改革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微積分精講I,II》這兩門課程的設置,就是面向數學基礎較好、敢于面對挑戰的學生,給學生更多的選擇,更多提升的可能性,并引導對數學有興趣的學生學好數學,培養數學人才。”而除了這兩門課程之外,潘教授對于日后的分析類課程,也有自己的想法。“今年倪老師主講《數學分析精講》。我們希望進一步建立精講課程系列,并在今后設立榮譽課程體系,以利于更好地培養優秀人才。”
潘教授上課的模式同其他教授不太一樣。他會提前上傳當周課件,上課時詳細講解其中最本質的部分。潘教授解釋道:“教學中要(兼顧)教學目標及學生的基礎和學習能力,努力做到課程的知識體系合理完整,內容豐富,敘述清晰易懂,使學生容易學,容易懂,使大部分學生能掌握課程的主要內容;又為好學生提供更寬、更深的教學內容,提高學生的數學眼光、水平、能力。”課程會提供一些較難的材料和問題,供學有余力的同學在課后自學和思考,不過作業和考試的重點依舊是那些重要的/本質的以及簡單易懂的內容。那些比較難的材料,按照潘教授的說法,是“心情特別特別好”的時候閱讀的東西。
不過,就像任何一門數學課一樣,同學們仍然需要做大量的習題訓練。潘教授說:“教學中應當兼顧學生學習基礎理論與訓練解題技巧。” 到了大學,數學系的同學們仍然需要在題目的訓練中逐漸掌握理論知識。
與之相對的,潘教授同樣也會在題目的設計上投入更多精力。無論是課件上的例題,還是作業中的附加題,潘教授都會精心設計,力圖以問題顯現更加深刻的數學思想。潘教授同樣提到,“考試應當注重考查對知識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每次考試都應當設計新題。”他也是這樣實踐的。
相比于其他科目,數學考試有更多證明題,會有若干不同的證明方法,計算題的解答過程也多種多樣,老師批改時不能只看最終答案是否正確,還要看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確,論證是否嚴密。潘教授講,“數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不僅要教數學知識和方法技巧,也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數學思維、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數學論證和表達的能力,訓練學生嚴謹的學風。”
在數學以外,分析能力和數學思維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潘教授對分析學有頗多見解,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互聯網時代,搜索快捷與信息易得,將使下一代人普遍知識廣博而淺薄,人人會套用公式,但不愿沉下心來深入學習以打好專業基礎,因而往往缺乏新思想。一些學校的教育往往迎合這個趨勢。我們現在要著力培養部分學生的分析能力和數學思維,使他們能提出新問題,提出新思想,才能讓他們在將來與眾不同,能面對未來的競爭,更能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
?
4. 人師之善:
春風化雨,以行動弘揚數學精神

潘教授在理工學院迎新會上,為同學們講解專業設置。理工學院/攝
在不少學生的眼中,潘教授平易近人,對學生格外關心。這同潘教授自身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教學不僅教課,還要關注學生人格、理想和心靈的培養。潘教授這樣闡釋:“教師不僅要做‘智者’,更要做‘仁者’,要對學生有愛心,關心他們的前途與目標,理解他們的困難。特別是這幾年疫情不斷,有些上網課的學生會有額外的困難,需要理解和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除了關心學生,潘教授更加重視以自身行動弘揚數學精神。“我們應當努力以自己對數學的熱愛以及對教學的激情感染學生,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和熱情;以自己的敬業精神和踏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和良好的學習習慣。”潘教授有時會在課堂上分享一些電影和文學作品,而這些作品似乎或多或少蘊含著數學的思考。這也正是數學的特點:數學不僅僅是定義與命題的堆砌,更包含了與世間萬物普遍聯系的思想。
在大眾的印象中,數學思想并非人人可得。談及“數學的天賦”,潘教授并沒有立刻接受這個說法,因為他并不能確定天賦對于數學學習的作用,現實中正面例子與反面例子都有不少。然而無論如何,潘教授相信,態度和主觀努力仍然是決定學術產出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不會偏袒有天賦的學生,并且強調要在教育上盡力做到相對公平。“我們應當尊重學生,努力做到對所有學生公平,一視同仁。”
但潘教授也承認,不同學生在數學基礎、學習節奏和學習速度上存在差異。潘教授指出:“對于優秀學生,指導他們加深學習,提高眼界,為今后的學習做準備。對基礎差的學生予以鼓勵和引導,指導他們改進學習方法,掌握課程重點,跟上課程進度。”這也是潘教授“因材施教”觀念的另一種體現。
潘教授對于學生的關心也影響著他的教育方法。“時代在變化,每一屆學生都有不同。教學方法相應要調整,以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潘教授注意到,面對長期的網課學習,最近幾屆學生似乎會比以前的學生更加需要忍耐孤獨。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不同屆學生對于自己所在集體的認知也存在差別。相比于過去兩屆,這一屆數學系的同學們,似乎對自己的數學水平有更高的自信。這些細微的差別,會讓潘教授調整自己的授課方式和授課風格。
?
5. 師徒之間:
學術漂流中的共同記憶
在接下來的幾天里,記者陸續采訪了數學系的幾位同學。他們分別是:大一的H同學,大二的X同學和L同學,以及大三的Y同學。他們獨特的故事中,或多或少帶著潘教授的影子。
大一的H同學很早就確定了學習更多數學理論的目標,并因此選擇了潘教授的課程。而他也希望挑戰自我,“我可能不是做數學研究的料子,但多學點數學總是沒有壞處的。”他解釋道。
半個學期的學習后,我問起H同學是否感受到了大學數學與高中數學的不同之處,H同學笑著說道,“我覺得從第一個月開始就已經不同了。我們第一節課學的就是ε-δ語言(數學中的一種證明方法)。相比于普通微積分課程,我們更多是在思維本身上劃一個缺口去進入。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實質的門在我面前:推開這個門,走進去,就是一個大學的數學世界。”
H同學的數學之路才走了半個學期。相比之下,X同學和L同學已經在這數學世界中漫游了一年,并確定了自己的專業。
X同學最終選擇了應用數學專業,可他也曾糾結是否要走其他的發展道路。X同學高中參加了生物競賽,對于生物建模等有一些興趣,而這一塊內容需要不少數學知識。所以進入大學后,他為了打好數學基礎,選擇了潘教授的課程。“我高中并不是搞數學競賽的,對于選擇數學是有些顧慮的,而(潘教授)這門課也不是特別容易,一開始有點跟不上。”后來潘教授告訴他,數學不像其他學科,需要一個比較長的積淀期。“當時確實是有動搖的想法,想轉去其他專業,比如生科(生物科學)之類的。但是后面感覺自己還能繼續往下學,并且還是挺感興趣的。”我問起他是否有意愿做數學研究,他說:“我覺得到后面是完全有可能的。我本科的打算就是一直學數學。”
L同學的故事則更加富有戲劇性。在一年的學習后,他從金融工程直接轉到了理論數學專業。在大學之前,他似乎便已經規劃好了自己的職業發展路徑:從本科金融工程,到北美量化碩士,再到投行或私募的工作。“有一些直系學長和我說我們學校的數學專業是很不錯的,所以我后來轉到了潘老師的課上。”在幾節課后,L同學發現了數學的獨特魅力。“我小時候其實是不太喜歡數學的,因為我很討厭計算。”但是L同學提到,他喜歡理科內共有的“獨立于經驗的理性知識”,而潘教授的課程,正是將他從小到大對于理性美的熱情激發了出來。
L同學稱自己是一個“咋咋唬唬”的人。他喜歡社交與熱鬧,在過去的一年里參與了各類社團、競賽、學生工作等活動。但在一年的嘗試與探索后,他還是更享受數學學習帶來的正向反饋,并且也知道自己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潘教授最欣賞我的一點是我的一些很‘跳’的思維。他說,我的很多奇思妙想是有好處的,是值得培養的;或者說,我還是有適合學習數學的地方的。”
一位大三的Y同學因為學業上的優異表現,給潘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Y同學在大二時選擇了理論數學專業,而如今她似乎正在考慮一些應用的方向。她對于數學知識的掌握仍然出乎我的意料——她對于那些學過的數學定理好像如數家珍,并能夠熟練地運用。雖然不再鉆研理論,但她仍能熟練運用學過的數學定理。
不同年級的同學似乎都能感受到潘教授所開課程的重要之處。X同學說道:“我覺得潘教授很適合教大一的課。一個很優秀的教授去教大一的課并不是什么大材小用。越基礎的課,往往是越重要的課,也越需要優秀的老師做引路人。”而Y同學也證實了這個說法:“大二和大三也一直在用大一的那些東西。大三那個勒貝格積分(大三的課程內容)其實和黎曼積分(大一的課程內容)是差不多的算法。大一(的課程內容)其實是最重要的。”
每一位同學都有自己對潘教授的獨特記憶。H同學提到潘教授“用幽默的語言對沖宣告quiz(小測)時間的情感沖擊”;L同學還記得潘教授展示的原創詩詞和電影推薦,以及課上給倪維明教授“打廣告”;X同學記得潘教授以類似“開火車”一樣的方式讓同學們回答問題,調動課堂積極性;Y同學記得潘教授用偏微分方程說明“跑步時女孩的馬尾只會在豎直平面內沿水平方向擺動”,以及“為什么操場都是沿著逆時針跑”。與潘教授的點點滴滴溫暖著同學們的學習生活,讓同學們的數學之旅更添生動和美好。
盡管同學們并沒有在課程之外和潘教授有專門的聯系,但每一次偶然的相逢都會留下記憶的種子。X同學提到,去食堂吃飯時經常能碰到潘教授。“我們會找他抱怨數學分析(大二數學相關內容)的難度;他這時就會來安慰我們,說‘學這些東西是我們的幸運’,因為學長學姐(由于課程改革帶來的變動)都沒學過這些東西。”他笑著回憶道。
有時潘教授也會主動聯系學生。潘教授舉辦偏微分方程的研討會時,特地給L同學發了一封郵件,說希望他去聽聽,因為“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其他人的研究方向”。而去年學校評選Student Award(大學榮譽獎項)時,潘教授也主動為Y同學寫了推薦信,希望她能參與競選,贏得獎項。
所有參與采訪的同學都表達了對潘教授的高度贊美。“他不僅數學專業水平高,還非常重視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各個層面的發展。”X同學這樣評價。而Y同學的回答更為堅定:“你大學期間碰到這樣一位老師,你的大學生活就值了。”
在眾多贊美聲中,H同學的回答與眾不同。“我一開始聽到學長學姐的評價全是正面的。我會覺得有些奇怪,就是真的有老師能做到零負面評價嗎?因為其他老師或多或少地,因為個人風格問題,會收到褒貶不一的評價。”在半年的課程學習里,潘教授于他而言,有了更加立體的形象;而他給出了自己的評價:“你聽到那樣的評價之后只會留下一個印象。但真的只有是接觸了之后,那種感覺是每個人心中都會有的。這種情感表達出來,就只有正面評價了。”
?
求索真理的修行
潘教授所面對的群體,即數學系的學生,本身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為數學的難度,他們常常被拔高和崇敬;但在如今的評價體系里,他們似乎永遠處在邊緣。當同齡人早早開始科研或實習時,他們仍然需要學習大量理論知識。隨著時間推進,課業的壓力、人生的抉擇、前途的挑戰同時壓在了他們的頭上。當他們焦慮、迷茫時,他們真的會需要交流和鼓勵。
數學系的同學想要申請應用方向和工科方向(的研究生項目),可能會遇到一些障礙:本科生很難在數學前沿做出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們的科研經歷在數量上不一定有其他學科的同學豐富;我們課業壓力也很大,沒有大量時間去做這些東西。”Y同學坦白道,“……就是說,那種有壓力的感覺,不是很好。”
剛進入數學系的X同學和L同學也感受到了與同齡人的脫節。X同學看到同齡人早早接觸科研與實習,感到了不同專業帶來的同輩壓力。而跨專業的L同學也壓抑住了自己躁動的一面,經歷了痛苦的轉型。在數學學習這條漫長的路上,他們需要一個指路人,幫助他們沉下心來,堅持走下去。
也許,潘教授不僅僅研究數學、教授數學,更親自背負了發展這門學科的使命。他需要發現更多對于數學有興趣的同學,并鼓勵與支持他們從事數學工作,盡可能緩解他們的焦慮,排除他們受到的干擾。
潘教授很像一代數學教授的精神縮影——純粹,敬業,思想深刻。Y同學和我說:“我覺得,數學系的老師,都特別好。”她也明白,學習數學的人本身也對這門學科有相當的熱愛,這些人一般都不會特別功利。
H同學也認同:數學本身即會塑造它的教學者和工作者,因為“它是一門特立獨行的學科”,而它的學者也會有相應的使命。“數學就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它必須要被走完,中間哪一步崴了腳都是會走不下去的。”H同學說,“潘教授應該也是注意到了這一點:當你真正想走這條路時,他會給你指出來這條路應該怎么走。”
無論是潘教授,還是這些數學系的學生,他們都在進行一場漫長的修行——沒有那么多榮譽和利益,只有數學真理帶來的極致的真誠;而正是這種真誠,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為之貢獻自己的智慧。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有理由保持著對數學的敬畏。





